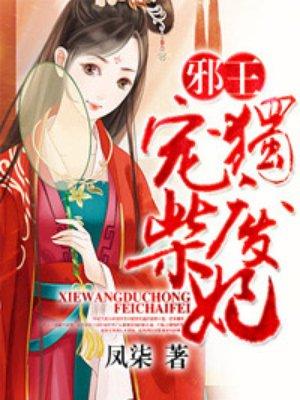九月小说>不及冬 > 第 39 章font colorred番外font(第9页)
第 39 章font colorred番外font(第9页)
咳嗽频率越来越高,他不想拖累她,想像剧里那些主角一样放狠话赶她走。
可他哪里忍心对她说狠话,哪怕是假的也不行。
尤其,她偷偷亲他,说他们就算吵架也不能分开,他更舍不得。
那就再自私一点吧,在最后的岁月里,再占用一点她的时间和关心。
夜里开始反复发烧,好像在提醒着他,时间不多了。
他让侯云景帮他将头发都剃了,买了两顶和他之前的发型无异的假发,一黑一白。
他每天断断续续地写信。
一封信,他写了整整一个周。
写完那天,他让侯云景带他出门。
在北城外国语大学附近的花店挨家挨户地询问他们的店能不能开到2022年6月份左右,他可以多付几倍的钱,务必帮他将花和信在办毕业典礼那天送达。
询问了不知几家,都不确定能不能经营到那个时候。
好在,两天后总算有人给了准确的答复。
之后,他打视频电话和瞿利安交代起了后事。
他很清楚这些年瞿利安是怎样过来的,以前用工作麻痹自己,知道沈已玲已经去世后,有空了就去墓地待一天。
瞿利安就想这么守着他和那个墓碑过一辈子。
他有些庆幸,他和林桑还没到有孩子这种羁绊的阶段。
否则,她一定会像瞿利安那般,时常看着那张与逝去的爱人相似的脸出神,用旧时记忆反复折磨自己。
想到以前奶奶骂瞿利安不成家以后连碑都立不了的话,他在确定有这个习俗,且花乌镇人都知道后,让他们在他走后,遵循这个习俗。
不办葬礼,不立碑,不祭奠。
瞿利安一口否决,说这个习俗只有信这些的人才会遵守,他向来崇尚科学,不信这些。
沈听原拿着手里带铃铛的胡萝卜钥匙扣说:“我知道,我就探探你口风。”
“反正真到了那天,你们这么告诉她就行,立碑了也别告诉她。”
“你们也不怎么回云亭,要立的话就别立在云亭了,万一哪天她去的时候会发现。”
“等我走了,其他东西你们随便处理了就行。”
他晃了晃手里的东西继续道:“这个,还有盒子里那个信封,记得跟我葬一块,我能带走的也只有这些了。”
“对了,还有个很重要的事。”
沈听原垂下眼,眼睫轻颤,随后低叹了一声道:“老人家身体不好,遭受不了打击,真到了那个时候,毕竟心连心,他们可能会有感应,但……”
“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。”
“……”
做完这些后,他又开始研究怎么用银杏叶做玫瑰花。
花做好后,他翻出那顶银白的假发戴上。
这样,诺言基本完成。
他也没什么遗憾了。
可林桑说要和他结婚,甚至连婚戒都准备好了。
他又想再自私一点,再多奢求一点。
反正,他们这场婚礼只有婚戒,没有任何仪式,没有见证人,没有亲朋好友,也没有领证。
一场盛大却无人知晓的婚礼。
不会影响她以后结婚。
……
高烧和低烧不停交替,越来越频繁,他视线越来越模糊,开始看不清他们的脸。